 恋水无痕
恋水无痕
共4条回答199浏览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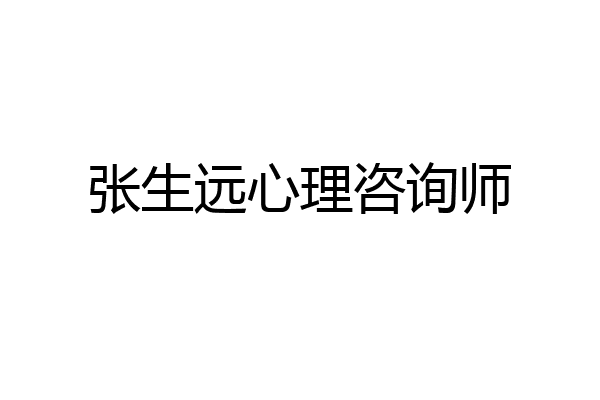
在《西厢记》中,崔莺莺与张生的第一次见面时在张生游览普救寺时不期而遇,彼时,崔莺莺在红娘的陪伴下捻花正欲往佛殿上耍去来。张生远远看见远处的佳人“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红娘发现有人“那壁有人,咱家去来。”面对红娘的慌乱与催促,书中用一个小小的括号写了崔莺莺的反应“旦回顾觑末下”,崔莺莺并未着急离去,而是回顾之后才施施然离开。就是这“临去秋波那一转”,让张生不顾功名,在普救寺常住,只为佳人。
-
-
 豆豆侠35小时前发布
豆豆侠35小时前发布-
张生形象的转变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反映了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转变角度来看:在唐代,国力强盛、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人学士养尊处优,倍受礼遇,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因此在《莺莺传》中张生的社会地位比莺莺的高,其自私负心的行为不免反映出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后来到了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重武轻文,读书人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处处受制。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也有所反映,连丫环红一娘一也称张生为“馋穷酸来”,可见其地位的低下,故此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张生对莺莺的追求会遇到众多外来的干扰,受到重重的波折与磨难。同时,由于市民阶层的`空前壮大,身处其中,自然而然地融合了民间百姓的审美趣味。在《西厢记》中塑造了一个语言明白晓畅,轻松诙谐的市民喜剧形象——张生。
张生形象的转变并非一个跳跃,他是经过不断地锤炼,更主要的还是受到市民大众的人生观念和审美情趣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重视生活上:张生本来要上京赶考,在巧遇莺莺后,他一反传统学子对仕途前程的追求,而将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义无反顾地追求莺莺。与拥有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思想的文人相比,张生是如此的热一爱一生活。他对自我理想及人生目标的追求,恰恰与潜藏在市民大众内心的人生观念一致,并产生共鸣,故而为市民大众所津津乐道。此外,还非常重视喜剧的娱乐作用:剧中张生并不是一个严肃正经的书生,而是一个生动而带有傻气的喜剧形象。利用故事情节的突变,充分向观众展现了张生的自身矛盾,在其前后行为抑扬一交一错的对比中,生动活泼地显露了他的“风魔劲”,嘲笑了他的痴、傻,从中表现张生身上志诚专一的美好品质。把张生塑造得生动有趣、诙谐滑稽,非常符合市民大众的审美情趣。由此营造的轻松惹笑的氛围,吸引了观众的笑声,使观众从中得到极大的娱乐与满足。于是一个生气勃勃、幽默诙谐的正面市民喜剧形象便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传诵千古。
六、结论
王实甫笔下的张生是文魁、志诚、傻角的统一体。张生的英俊潇洒、富有才学和胆略,为他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婚姻提一供保障。他的志诚是他克服外界各种阻力,冲破重重障碍取得爱情的关键。他的傻气既源于他对莺莺的深情,又使他更加生动可一爱一。在戏剧冲突的不断形成与演变中,充分地体现了张生一性一格的复杂一性一与立体一性一,给人留下鲜明生动的深刻印象。张生的一切言行皆是真心的流露,他的形象拥有着人性的光辉。
张生这一人物的典型一性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后世许多爱情题材的文学创作。如在同一时期的《墙头马上》的裴少俊,或稍后的《倩女离魂》的王文举等许多作品中主人公的创作都深受其影响。《西厢记》中张生的叛逆精神更令后世许多名篇巨著如:《牡丹亭》中的柳梦梅、《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等所继承和发扬。在他们的共同鼓舞下,激励着后世许多青年积极追求爱情婚姻自一由 ,勇于反抗封建礼教。并且共同聚集成一股力量,共同讽刺与冲击着封建礼教与封建制度的堡垒。
张生人物形象分析 [篇2]
整体而言,张生在《西厢记》中,是一个温文尔雅、执着志诚、略带傻气的书生形象。他虽是一介书生,书剑飘零,但又是文章魁首。他凭着自己的英俊潇洒(外表的)和聪明机智(内在的)深深吸引着莺莺,并且也以此为资本热情而执着地追求着莺莺。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张生甘愿放弃功名,面对困难仍不屈不挠、毫不退缩,是元稹《莺莺传》中的张生远远不及的。正是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张生爱情至上的一面。
普救寺拈香,莺莺首次见到张生,就叹“自见了那张生,便觉心事不宁”。这也只因“想着文章士,旖旎人;他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不由人口儿里作念心儿里印”。莺莺是父亲在世之时,许配给舅表亲郑恒的。按封建常理,莺莺对张生应“非礼勿视”的,更不要说动了性情,心神不定。然而,这又是一个很真实的现象——虽萍水相逢,但已经被对方的俊美外表所吸引。
张生的“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也仅仅是吸引莺莺的一个方面。他首先为莺莺所注意者,还是他的才情。张生太湖石畔吟诗“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即景寄情,既抒内心寂寞、孤独的情怀,寄托了相思之情;又描写了眼前月色兼试探莺莺。全诗字句清新,情景交融,意境清幽典雅,以至莺莺赞道:“好清新之诗。”并不由和诗一首。正因这首诗,莺莺才有后文“学得来‘一天星斗焕文章’,不枉了‘十年窗下无人问”这样对张生的认知。
如果说,长相俊美、诗才敏捷也只不过是一个优秀书生的本色,那么,张生解孙飞虎之难,却显示了危难之际,过人的胆识和才略。“笔尖儿横扫了五千人”“半万贼兵,卷浮云片时扫净”。也许是本性如此,也许是对莺莺志在必得,张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书生的镇静和从容,也使他赢得对莺莺母亲道义上的胜利。
但是最终使莺莺以身相就的,恐怕还是张生为了莺莺先是“昼夜忘餐废寝,魂劳梦断,常忽忽如有所失”甚而要“就小娘子前解下腰间之带,寻个自尽”继而“卧枕着床,忘餐废寝,折倒得病似愁潘,腰如病沈”的表现。这样的痴心,这样的志诚,这样的“自我摧残”,深深打动了莺莺。
总之,是张生外在的与内在的各种素质,使他得到了莺莺的心,也得到了莺莺的人。而“小生不往京师应举也罢”也一直被认为是张生把爱情看得高于科举功名的证据。
-
-
-
有一个女孩名叫茜,在她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她的爸爸就已经去世了,她和妈妈、姥姥、还有继父生活在一起,可是姥姥和继父都不喜欢她。于是,在她上高中时妈妈给她送进了一所私立学校。私立学校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在这一群富家子弟中,茜显得是那样的另类,她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这些钱只够她一个月吃饭的花销,所以,她每天都等同学吃过饭后,躲在一个角落里吃馒头和咸菜。但女孩从就要强的性格让她在学习方面很突出,她每一次考试都是全年级的第一名,许多有钱人的家长都希望她能给自己的孩子补课,但是,她看不惯有钱人家孩子的样儿,所以,都被她拒绝了。 没多久,班级里一个名叫巩的男孩对茜说:“你帮我补补课吧?”茜不屑的笑笑,说:“我为什么给你补课?”巩理直气壮的说:“因为我成绩差!”这句话使茜多看了他一眼,就是这么一眼让茜觉得巩与众不同,因为巩和别的有钱人家的孩子不同,他身上总是穿着一件破旧的大衣,而且也没有贵族人的傲气,于是便答应了给他补课。每天茜都给巩补习功课,同时也增加了茜的收入。渐渐地,他们熟悉了,得知巩的生日是12月31日一年中的最后一天,而茜的生日是1月1日一年中的第一天,巩开玩笑的说:“我比你大了整整一年啊!”茜冷淡地回了一句:“仅一天而已!”这一天放学,学校门口停了一辆宝马,许多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没有见过,那是巩的家人来接他了,茜看着巩走向了车的方向,心想:“为什么他们可以那么有钱?为什么他们就可以开宝马?”就在这时,巩回头对茜淡淡地一笑便上了车。茜回过神来想:“我为什么要羡慕他?他又没有我学习好!”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尽管茜每天都给巩补课功课,可巩的成绩一直也没有明显的进步,离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们都顾着自己的总复习,也不再补习了。茜一心就想考上清华,因为她不想被别人看不起。考试成绩出来了,茜如愿地考上了清华大学,并且是高出全校第二名整整50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 由于学校还没有开学,茜想回家看一看妈妈,她们母女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面了。可她刚进家门,继父见了她就又打又骂的,妈妈把她护在身后,无奈之下茜离开了家,当她走到楼下抬头看着自己家的阳台时,她多么希望在临走前再见妈妈一眼,可等来的却是姥姥把她所有的行李丢了下来,她伤心的离开了家,又回到了北京。 茜回到北京后,准备死处找房子,正在这时她看见一个老奶奶在收拾一个库房,她走上前去问:“老奶奶,您这房子租吗?”老奶奶笑眯眯地说:“小姑娘,你想租房子吗?”茜点了点头,“那就100块钱吧!”老奶奶回答她。茜正收拾房子的时候,见到了很久不见的巩,茜不想让别人看见自己落魄的样子,生气地问:“你怎么在这儿?”巩还是和以前一样穿得随随便便的,表情怪异地说:“我来看我姑奶奶!”茜像被看穿了一样,一直沉默不说话。巩问:“听说你考上了清华,恭喜你啊!”茜也不是那种不识价的人,就说:“谢谢!那你呢?”巩不高兴地说:“我爸爸让我出国!”茜冷冷地看着他,狠狠地说:“哼!你们有钱人家的孩子就是这样!”巩又接着对茜说:“你愿不愿意帮我一个忙?”茜疑惑地问:“什么事?”巩说:“愿不愿意到我妈妈的公司做打字员?”茜立刻就生气地说:“你是在同情我吗?”巩急忙解释:“不是的,我妈妈的公司最近效益不好,许多员工都走了,现在正好缺人,你就当是帮帮我,好不好?”茜答应了,每天都去巩妈妈那上班,一个月发600元的工资,这对她来说已经很满足了。巩就要出国了,在巩走之前茜请了他吃顿饭。 巩出国了,茜依旧每天一边上课一边工作,现在每个巩月的工资已经可以达到2000元了,并且巩的妈妈怕她跑来跑去的不方便,给她配了一个笔记本电脑,在别人看来都以为她很有钱,当然了,茜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过。 在茜的寝室有一个北京的女孩,个性比较刁蛮,但是从来不欺负茜。茜还是同以前一样的要强,受不得别人的学习比自己强,可这一次她遇到了对手。有一个叫林的男孩,每次的成绩都要比她高,茜很不服气总想超过他。在一次复习课上,茜心里想:下一次考试我一定要超过他!就在这时,老师问了一个问题并叫茜来回答,可由于茜精神没集中连问题都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摇了摇头。老师又问:“有没有人会这道题?”……林主动地站了起来回答了这道题并受到了表扬。茜恨恨地想:你以为我不会吗?用你来告诉我?下课了,茜把林截住说:“下次考试我一定会超过你!”当时在场的同学都感到很惊讶。考试成绩出来,茜果然取得了第一名,茜在成绩单上寻找着林的名字,却发现林的每科成绩都是零分,她很生气:不愿意和我比就直接说嘛!宿舍的女孩告诉茜,林在校园的湖边等她,她愤愤地跑过去说:“你什么意思?这算什么?”林没有说话,只是把手中的卷子递给了茜,茜疑惑地问:“你怎么会有卷子?”林说:“我姑姑是教务处的……”还没等他说完茜就打断了:“你们有钱人都是这样!怪不得每次成绩都那么高!”林不慌不忙地解释:“可我从来就没有动用过这种关系,卷子我已经答完,你可以合一下分数!”茜拿卷子算了一下总分还是比她高,她很是不解……林突然抱住了她,对她说:“我喜欢你!”一个女孩被男孩抱在怀里,她所有的骄傲都没有了,于是他们开始交往了。没多久他们就发生了关系,每一次出去茜都要给林钱,因为两个人出去男人付钱总是有面子,时间久了,她每次都会给林零花钱,这在他们之间也成了很普通的事情。茜的生日就要到了,茜幻想着林会送她什么礼物,心想:给他的零花钱已经足够给我买一个项链或钻戒的了。她想想就觉得很开心! 茜生日那天,林一天都没有联系她,她以为是林故意的,为的是给她一个惊喜。这时电话响了,茜拿起电话说:“你死哪儿去了?”只听见对方惊讶地说了一声:“啊?”她问:“你是谁啊?”“我是巩!”她生气地说:“怎么是你呀?”巩淡定地说:“祝你生日快乐!”“谢谢!没有什么事先挂了!”巩说:“那好吧!再见!”巩并没有等到茜的回答,而是对方那边传来嘟嘟嘟嘟的声音……电话又响了,是林打来的,接过电话后,茜急急忙忙的跑到楼下,可是,林看起来很不开心的样子。茜心想,可能是他想给我一个惊喜吧!林问茜:“晚上可不可以不回去?陪陪我!”茜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到了酒店,茜才知道原来悲伤、痛苦的表情是不可以伪装的。林对茜讲了一段她最不想听到的故事:林原本有一个女朋友叫蕊,在一所电影学院,他希望他的女朋友和其他的女孩不一样,希望她不被世俗所感染,但当他去找蕊的时候,她却和一个有钱人走在了一起,说着贬低自己的话,可林并不甘心。上午,林用积攒下来的零用钱给蕊买了一个钻戒,结果却被蕊丢了回来。茜手中拿着那枚钻戒,看着上面刻着一个“蕊”字,这一刻,茜好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要那么努力的读书?为什么要认识字?如果她不认识字,她会认为那个字是她的名字,可是,茜忍住了泪水,安慰着林说:“没事,没事的!”没多久,茜不在巩的妈妈的公司工作了,由于她所学的市场营销管理正是巩的爸爸公司所缺少的,所以,她又到巩的爸爸公司上班。眼见就要毕业了,大家就要各奔东西,茜和林也就分手了。 茜随着巩的爸爸来到了深圳发展,几年的努力茜已有了很出色的表现。经过各种关系,现在茜已经是英国总公司在中国分公司的经理。茜为自己买了房子、买了车,她只是为了证明别人有的东西自己也会有,但只是时间的问题。 巩在国外回来了,请家里人在一起吃饭也包括茜。茜看见巩还是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种拉里拉遢的,没有什么上进。吃过饭后,茜问:“你去哪儿?”巩回答:“白天鹅!”茜又讽刺的说:“你们有钱人总是住那种星级酒店。”巩并没有回答茜的问题,而是问她:“可不可以陪我上去?”“为什么?”巩哀求着说:“就算是求求你了,陪我上去,好不好?”茜想了想答应陪他上去,刚进屋门,巩说:“把眼睛闭上!”倒数5个数!当茜睁开眼睛的时候,在屋的角落里跳出了许多的小丑为她弹琴、唱歌。这时,巩推出一个五层的大蛋糕走到茜的面前:“生日快乐!”茜好感动,因为她已经好多年没有过生日了。巩手中拿着钻戒单膝跪在地上认真地对茜说:“嫁给我,好吗?”茜说:“给我个理由!”“我爱你!”巩回答。茜点头答应了,但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样是对是错,因为她还是没有办法忘记林,但是,巩的父母对她也很不错。没多久,巩和茜结婚了。 结婚以后的茜还是同以前一样整天的忙于工作,而巩却是在家养养鱼、养养花、上上网,这让茜很看不惯,有一次茜不平地说:“为什么我整天的在外面奔波,而你却整天在家闲着没事!”巩笑嘻嘻的说:“要不我们都在家吧!反正,我爸妈挣的钱够咱俩花一辈子的了!”话音刚落,茜就生气地吼道:“为什么要花你爸妈的钱?难道我们没有能力挣吗?”巩见老婆生气了,急忙连笑带求饶的哄茜。每一次都是这样。一天,茜的QQ上有一个陌生男人加她,她隐约地感觉到那个男人是林,但她还是加了。结果真的是林,他们聊了很久,茜得知林在西北的一家公司当经理,她就觉得自己的老公太没出息了。 回到家以后,茜看见鱼缸里有一只鱼腹朝上了,她就捞出来扔了。巩回来以后发现少了一条鱼,就问老婆:“我的‘二姨太’呢?”茜冷淡地说:“我看见它腹朝上就扔了。”“不是,它每天都这样休息一会儿的!”茜听了以后气急了:“你整天就知道在家呆着,就不和别人一样?”巩听了以后,没有一丝表情的问:“你说的‘别人’是他吗?”茜伸手给了巩一个大嘴巴,巩没有说一句话,把门轻轻地带上离开了家。已经两天了,巩都没有回家,茜也知道自己确实有些过分了,但又不好意思主动打电话,她忽然想到了巩的那本日记,巩一直都不让她看,这一次她可以看看了。 打开日记,第一页: 年X月X日,我们班有一个女孩她和别人不一样,每次同学吃过饭后,她都躲在角落里吃馒头、咸菜,我很想去帮帮她,可是,她好象很讨厌有钱人家的小孩,我得想一个好办法! 今天我让爸爸给我弄了一件破旧的大衣,我想这样就容易接近她,她也不会讨厌我了。她已经决定给我补课了,为了能和她在一起的时间久一点,我故意每次都考不好,虽然每次她都说我笨,但我还是很开心。可就是无法向爸妈交代。 我的生日到了,爸爸开车来接我,我有点不高兴,因为我怕她会因此疏远我。明天是她的生日,我多希望叫她一起上车,但我知道她一定不肯,所以,我只能送给她一个无奈的微笑。上了车以后,我脱下了破旧的大衣,换了一件新衣服,爸爸还说我是不是有毛病,总爱穿这件破旧的大衣。 “我觉得我已经喜欢上她了!” 爸爸妈妈知道我喜欢她了,但爸爸说只要我考上清华就同意我们在一起,所以,我开始努力的学习。但是,她那么要强,我不能超过她的分数,所以,我把每一科都少答了几道题,就这样,我比她少了整整50分,考了全校的第二名。可爸爸让我出国,如果我不同意,他会把我帮助她的真相全部告诉她,所以,我答应了!出国前我见到了她,我邀请她到我妈妈的公司做打字员,我怕她知道我是故意帮她,所以就和妈妈商量了一下说公司效益不好。在我走之前,她说要请我吃饭,我说我吃牛肉面,她不同意,我就说我最喜欢吃牛肉面了,因为我知道即使我们两个人都吃才要3块钱,那样的话这个月她还有597块钱的零花钱。吃过饭后,她回学校了,没走多远我就吐了,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饭。 太巧了!她宿舍有一个女孩是我的初中同学,我告诉过我同学不许欺负她,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在同学的口中得知她有了男朋友,我很想问问她最近好不好?但是,我却找不到打电话的理由! 今天她的生日,我终于有了一个打电话的理由,但是,听她的生意觉得很急,好象在等人,所以匆匆的就把电话挂了。同学告诉我,她今晚没有回宿舍,我好害怕,我真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心好乱! 在国外,我努力地奋斗,但是,我却不能告诉她我的成就,我怕她会因此不理我。我经过了一番打拼终于使自己的公司在中国有了分公司,而总经理就是她,我自然就放心了!我就要回国了,我却不能告诉她这些年我的努力。但是,不管她现在还有没有男朋友,我都要向她求婚。 我向她求婚了,她答应了我! 结婚的那天晚上,我故意把自己的手指割破,把床单染红了,尽管我和她的心里都明白她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在我的心里,她永远都是那个我要珍惜的人。 结婚以后,她依旧整天忙于工作,而我不能一天见不到她,所以每天只用电脑和总公司的副经理联系,尽管在她眼里我没有出息,但只要不伤害到她比什么都好。 我感觉她又和他联系了,我好怕我会失去她,因为我现在真的不能没有她,我想就这样和她过一辈子。 老婆,我真不想失去你,因为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茜已泪流满面,身边这个男人为了帮助她是多么地用心良苦,付出了那么多!她再也不顾忌面子,给巩打了电话,说:“老公,我知道我错了,回来吧!”“给我个理由!”巩问。“我爱你!”
-
-
-
《西厢记》故事,最早起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书生张珙与同时寓居在普救寺的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后来张珙赴京应试,得了高官,却抛弃了莺莺,酿成爱情悲剧。亦相传为元稹假借张生的自传体小说或故事。这个故事到宋金时代流传更广,一些文人、民间艺人纷纷改编成说唱和戏剧,王实甫编写的多本杂剧《西厢记》就是在这样丰富的艺术积累上进行加工创作而成的。历史上,“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美好的愿望,不知成为多少文学作品的主题,《西厢记》便是描绘这一主题的最成功的戏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