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晴天2030
晴天2030
共5条回答247浏览
-
 厚德悟远1小时前发布
厚德悟远1小时前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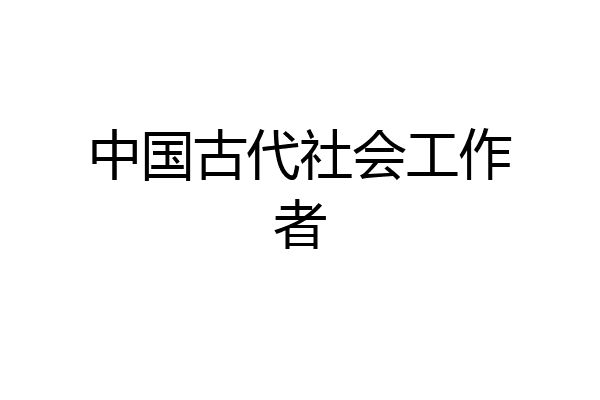
汉人治理社会的模式,有没有知道的。控制消费资本和商业资本,引导实业资本的投资规模和方向,街面上的店铺减少三分之二以上。撤销村乡两级政府,乡政府合并至市政府工作,原乡政府的住址上仅保留司法及人大的部分职能机构。兴办私学,公学不超过五年。告老还乡,资金回流,人才回归。实业救国,轻商自治,公学私办。政治上实行政府官员告老还乡制,废除分权制封地制,恢复饥民上访制,经济上实行遗产税制,农村修下水道拉动经济发展。汉人泰兴高东波
-
-
 艾米莉郡主8小时前发布
艾米莉郡主8小时前发布-
绅士当然指有风度了说的话很经典:精辟 妙语连珠
-
-
-
中教联盟老师:社工组织的成立和演变很复杂,最早应该是从西方的宗教中衍生的,是一种慈善性质的。开始的初衷都是好的,但是伴随时间就有一些变换。找了一些大概的,没有太具体的,要是写论文的话去找一些相关的书和论文看一下,要是只做了解的话知道是西方宗教衍生,在中国的传递。我也给你找了一些,你看一下吧。美国城市中最早的社会福利机构出现于19世纪中期。 世界上第一个睦邻馆是1884年在伦敦建立的汤恩比馆。 睦邻组织运动的重点是改造环境。 第一批拿工资的社会工作者是慈善组织协会的执行秘书。 1917年出版的《社会诊断》(Mary Richmond著)是第一本有关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的教科书。该书集中于个案工作。【1,研究(收集信息);2,诊断(发现问题);3,预后和制定治疗计划(确定帮助案主的具体做法)】我国社会工作的各个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萌芽期——个人的慈善事业阶段(20世纪上半叶社会工作开始在我国 起步发展) 1.教育方面: (1)标志性事件:1925年燕京大学建立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 (2)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军事和文化侵入以及中国人自觉向西方寻求民族自救的道路,西方文化也以各种方式进入我国。20世纪初至20~30年代,一些传教士在我国开办社会服务,并在我国的大学讲授社会服务等课程,一些大学开始从事社会服务教学并从事服务实践活动,这样,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开始出现。1925年燕京大学建立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可视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标志。 2.社会服务方面: (1)标志性事件:晏阳初倡导并极力推行的华北平民教育运动。 (2)一些上层社会的人士开展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孤儿救助、贫民救济等活动。另外,一些在西方受过正规教育同时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为了救国救民也从事农村发展活动,其中以晏阳初倡导并极力推行的华北平民教育运动最为典型。这是我国知识界施行的、具有一定专业性质的社会工作实践活动。虽然因战争等原因,这些实践活动的效果是有限的,但它对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40年代,当时政府将社会工作引入我国,对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 (二)第二阶段:断层期——受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造成发展的断层。(1949年至改革开放期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出于对社会学、社会工作的错误理解,1952年政府决定在大学里取消社会学、社会工作学科和相关教育,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中断。 (三)第三阶段:发展期——有组织的开展社会活动(改革开放至90年代末期间) 年国家民政部为了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在北京马甸举行了社会工作教育论证会,确认了社会工作的学科地位。 2 年,国家教委决定在部分高等学校试办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在制度上开启了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讲程。国家教委首先批准了北京大学设立社会工作专业。 年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成立,1994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成立,推进了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进程。 4.1992年正式加入国际社会工作者协会,这可视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或教育)的开端。 5.高等学校则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方面矢志不渝,并探索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道路。 6.不同部门也在进行社会工作专业培训,如民政、妇联等。 (四)第四阶段:专业化时期——科学的专业服务阶段。(21世纪至今) 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在此阶段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积累,使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突飞猛进,进入高速、专业的发展期。于是在这个时期我国社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在专业化、职业化和法制化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故作详细分析。 1.建立、健全职业化体制 (1)标志性事件: 2006年7月,人事部、民政部联合发布了《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首次将社会工作者纳入专业技术人员范畴,为进一步提高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专业化水平提供了制度保障。 2007年12月,民政部按照上述文件要求编写的《全国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大纲》正式发布,相关考试于2008年6月底在全国举行。首批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即将在我国诞生。毫无疑问,上述几个重要文件的发布、实施及专业社会工作者的诞生,是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建设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影响深远。 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指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制定人才培养规划,加快高等院校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抓紧培养大批社会工作急需的各类专门人才。这就对社会工作制度建设作出了全面规划,并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 (2)制定了相应的社会工作发展规划和发展目标,有计划、分步骤地推动社会工作在儿童服务、青少年服务、老年人服务、残疾人服务、家庭服务、社区建设、矫治服务、医疗卫生等各领域的发展,实现社会工作的多元化和专业化。 (3)建立包括资格认证、从业规范、登记管理、继续教育、评估监督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工作职业制度,推动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 (4)设置相应的行政管理机关,构建社会工作的行政管理体制,统筹协调社会工作的发展。 (5)增加“政府购买服务”等用于社会工作发展的财政预算,创建有利于社会工作发展的财政体制。建议在每年财政支出的公共服务项目的预算中,划拨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于社会工作事务的固定投入。并根据社会的发展情况,参考GDP的增幅,按比例提高社会工作的经费投入比率,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有力的财政保障。 2.推进和加快社会工作法律制度建设 (1)标志性事件:2006年民政部联合人事部在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大力加强社会建设的大趋势下,民政部抓住机遇,联合人事部正式出台了《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国人部发[2006]71号),这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标志着我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制度的正式建立。 (2)法制化是社会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一些社会工作比较发达的国家及地区,均建 3 立了完备的社会工作法律制度体系,从根本上确定了整个职业体系的合法地位。然而,我国社会工作事业刚刚起步,各项法律法规亟待建设。从社会工作发展的长远来考虑,应重视社会工作的立法研究及实践,加快社会工作的法制化进程,确立社工的职业地位,维护社工的专业形象和职业尊严;保障社工的职权及执行力,提高社工的工作效率;保障社工在工作中的合法权益,降低社工的职业成本及风险。 3. 实践和确立社会工作运行机制 (1)标志性事件: 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指出要建立健全以培养、评价、使用、激励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措施和制度保障,确定职业规范和从业标准,加强专业培训,提高社会工作人员职业素质和专业水平,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 (2)以社区为平台,以各类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为载体,以专业社会工作者为抓手,创建“社区、社团、社工”三社互动和“社工、义工”两工联动机制,确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民间运作、社工引领、义工服务、群众得益”的社会工作运行机制。采取一种科学化、专业化、人性化、大众化的方法开展公共事务的管理,逐步理顺社会工作与政府、社区、机构、居民间的关系,形成运转流畅、资源共享、和谐互动的工作运行机制,促使政府转变职能,降低管理成本,整合人力资源,扩大社会参与,推动社会民主法制的进程。 (3)设立配套的社会工作激励机制。设置专职社工岗位,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薪酬制度,以“体现专业人才价值”为指导思想,设计及实行一套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工作激励机制。在薪酬设计上,采取学历、资历、资格、业绩、岗位等多种指标相结合的方案,“以岗定薪、以绩定奖、按劳取酬”,设立合理的社工薪酬标准,使其高于同等工作的一般从业人员,合理体现社工的专业人才价值。 (4)具体来说有以下四种实施办法: 一.建立职业资格制度。如2003年3月,上海市民政局会同市人事局出台了《上海市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认证暂行办法》,将社工列入专业技术人才,规定每年组织一次社会工作师和社会工作师助理的资格认证考试。 二.建立注册管理和继续教育制度。如上海市出台了《上海市社会工作师(助理)注册管理试行办法》,对取得社工职业资格的人员进行注册管理,使其成为注册社会工作者,以促进社工的职业发展,规范社工的职业操守和实务工作。 三.是建立岗位配置制度。如2004年,上海市民政局出台了《关于在本市民政系统及相关机构配置注册社会工作者的意见》,明确提出在社会福利机构、社区公益组织配置社会工作者,并要求采取内部培养与外部引进相结合的方式力求上述目标在3年内到位。 四.是探索建立岗位轮训制度。如协调社会工作各领域的有关部门,共同对实际在岗人员开展分期、分批、分层的岗位轮训。 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是社会工作知识和经验不断积累和发展的反映,也是社会工作领域不断扩大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不断创新的过程。随着社会福利政策的全面化、系统化及社会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建立,社会工作逐步走向成熟。 三、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特点 (一)非一般发展规律,开始由政府主导起步,而非民间志愿的慈善事业先行起步。通过民政部主导的与北京大学的合作而开始了中国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发展的进程。与先有社会需求,再由民间发起,并以慈善组织出面组织对贫弱阶层的社会服务,然后再向专业社会工作转变模式不同。实际上,当时民政部的目标就是培养若干掌握社会工作与管理知识的人才,然后到民政部门从事“民政理论研究”,着眼点并非一线的实务工作者。于是,社会工 4 作与管理的专业教育就在既没有公众认可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合适的社会载体的情况下,突如其来地“被恢复”了。这样的恢复和发展,其实是与“社会”脱离的。如果用现在“制度嵌入”的理论来解释的话,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在中国的被恢复,表现出一种“硬性嵌入”特点。 (二)发展过程中,民间组织表现并不活跃,政府协调社会工作中起主导作用。造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是首先我国社会工作起步工作就是由政府的民政部主导完成的,所以对历史发展模式的依赖导致这一现象;其次政府对民间组织的信任还没有建立起来。改革开放前30年中期有一很客观的实例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当时中国除了一部分从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教育的教师还算得上“内行”之外,并没有专业社会工作者,但却有了社会工作者的“自己的组织”。实际上,这个组织并不是为社会工作者成立的,而是为了方便民政部门对外交流而成立的。在“民政工作就是社会工作”的观念的影响下,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被纳入”社会工作者的行列。 (三)“跳跃式”发展模式。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借鉴国外多,自主创新少;政府引导多,自我实践少。可以看到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开始发展至改革开放前期都没有很大的进展,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却是突飞猛进的,社会工作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种短期内跳跃式的发展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取外国的先进经验得来的。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社会工作的推进主要是由政府完成的,而政府在一些事情的觉得上具有社会实体、社会各团体所不能具有的强制力,所以形成“跳跃式”发展模式。 (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工作就表现出政府积极探索、社会工作教育率先发展、行政性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同时并存、专业社会工作不断发展的特点。
-
-
-
以儒家治国思想为主体的治理观念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赖以依存的思想条件,正是由于传统治理观念的存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过程才有了真实的意义。传统治理观念在客观上规范和制约着历代王朝的治理过程并决定其基本走向。首先,儒家重教化而轻刑罚的治国方略,追求善治、善政而拒绝暴政,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生活走向文明的发展路向。两汉以后,儒家重德教而轻刑罚的思想主张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治国理念,也成为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制定政治、经济政策的依据。对于每一代王朝的统治者来说,一旦他们接受了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并且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自觉地遵循这种理念,善治便有可能成为事实。据唐人吴兢撰写的《贞观政要》,贞观元年,李世民曾对臣下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此后至贞观四年,全国仅判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贞观政要·刑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38—239页)唐代贞观年间之所以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治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重教化、轻刑罚已经成为统治集团的自觉意识。诚然,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倡导的治国理念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为统治者所信奉,也不能在根本上杜绝暴政,但不可否认的是,儒家重德教、轻刑罚的治国理念,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规范着古代中国的治理过程。如果没有传统治理观念的规范和约束,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将是另一种情形。其次,古代思想家重视国家统一的治理观念,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制度安排。古代中国人所理解到的“中国”始终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诸子集成》第二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2页),古代中国所以能够从小邦林立的状态走向统一,其深层的原因在于人们观念中的国家是统一的。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刚刚走上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秦汉时期,如何维持统一是没有答案的,在那个历史时期,对统一的政治格局的最有力支持便是统一的观念。国家统一的观念体现在秦汉以后的治理过程中,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不断调适和完善。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是与郡县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相辅相成的。在秦以后的两千多年间,为郡县体制提供最有力的理论支持的便是古代思想家重视国家统一的治理观念。再次,传统治理观念中的富强追求,为历代王朝的变法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持。传统治理观念中的富强追求,是对中国古代社会治理过程影响最为深刻的思想要素。秦汉以后,历代王朝曾经有过多次变法,几乎每一次变法的推动者都把富强作为理由。例如,西汉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在为盐铁官营政策辩护时说:“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故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罢之不便也。”(《盐铁论·本议》,《诸子集成》第七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历史地看,汉代盐铁官营政策还有待于我们站在现代的立场上加以审视,但把“富强”作为政策理由却是历史事实。在中国古代社会,“富强”也是人们在主观心理层次上最可接受的理由。就秦汉以后历代王朝的变法而言,并不是每一次经济上的改制变法都会带来富强的效果,但是,在基本的社会安排趋于稳定的中国古代社会,变法无疑可以为这个社会增添某种活力,而传统治理观念中的富强追求,恰恰是这种活力的真实源关。
-
-
-
摘要:对于中国社会的考察,要接续潘光旦、费孝通等前辈的学术路径,回到传统社会分析的古典范畴。传统社会由殷周、秦汉之变,以及后续各代的发展变迁,均围绕着封建制与郡县制的辩证关系而展开。封建一方面以宗法、丧服、宗庙等礼制,以亲亲、尊尊的差等秩序为原则,确立了君统与宗统之间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则以天命的神圣观,确立了君民之间的自然天养的普遍法则,使民彝与民生成为了根本的治理基础。郡县则强调战国以来的历史势变,革除了封建制各私其土的乱政之源,反而开创了一个“公天下”的世界,确立了一种超国家形态的帝国政制体系。近世以来,王夫之、顾炎武等强调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旨在依据圣人对于三代之制的理解,打破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的集权制系统,重新理顺“公”“私”之辨。不过,对于经学意义上的封建的考察,仍是一件需要进一步推敲的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