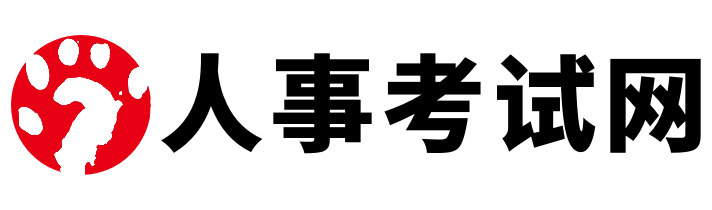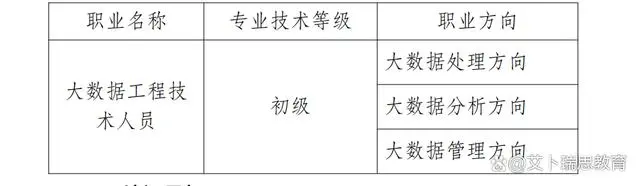我的教师生涯(一)
吴延东(广东)
1975年1月,我从官庄公社中学毕业。9月,怀揣着把青春献给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理想,我回到了曾经读过小学、初中的母校河上寨学校,当了一名民办教师。从此,我开始了漫长的教师生涯。
1. 教师的职业生涯始于教学点
在我高中的两年里,母校发生了新的发展和变化。
随着母校新址班级数量的增加,又新建了几间教室。母校二郎庙的两间教室全部拆除,部分砖瓦、木材运到新校舍建设,剩余材料在旧址东侧100米的何庄前新建了一个有两间教室和教师办公室的教学点。
我之所以能在这个教学点任教,全赖老校长的信任和机缘巧合。
我的母校,建校之初增建的几间教室都成了危房,三年级的两个班就被临时分在两个教学点,老校长把我推荐到队伍里,我便顺理成章地到教学点去给学生上课。
该教学点原有两间教室、两个班,现两间教室中间老师办公的小房间被用作一年级的教室。
教室里,除了一块漆得斑驳的黑板,几张土砖砌成的长桌,以及学生们搬来的小凳子和椅子外,剩下的值钱的东西,就只有粉笔、红墨水、练习本、课本了。
教学点虽然简陋,但环境优美。四周都是农田,路边自然生长的牵牛花、野菊花长势极强,顽强的藤蔓和茎秆毫无顾忌地爬上路面、地面。教室门前是一片小小的杨树林,一个小小的操场,一池水。师生们每天都能听到树丛中杜鹃、喜鹊清脆的歌声;蹲在水池边,舀一捧清凉甘甜的泉水,洗手洗脸,甚至吮吸进嘴里;站在水池边,在清澈的水中互相欣赏着对方优美的身影。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啊!
开学第一天,我们三位老师把三间教室重新装饰一新,黑板上方贴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像两边是毛主席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黑板左侧墙上贴着各年级的汉语拼音表,黑板右侧贴着一年级的加减运算公式表、二年级的乘除运算公式表、三年级的数学运算法则表。
当时推行数学“三算”,即心算、笔算、珠算相结合和汉语“国语化”教学。
有一次,我到龙泉学校听“三算”示范课,一大早沿着白通渠走了近二十里路,七点钟就到了,八点开始连续听了两节课。
真的很佩服李老师!分析问题时,他鼓励学生结合珠心算口算;指导学生做作业时,他强调口算、计算步骤。听李老师的数学课,就像看一场独幕教科书戏剧。
普通话主要以拼音教学为主,在学校学过一些拼音知识,但我知道远远不够满足教学要求。比如“一音轻,二音重,两音碰撞剧烈”;“一、七、八声相同,但去声变为阳平”等,这些教学规律都是听了博学老教师的培训课才学会的。
现在,我仍然记得我教过的一篇二年级课文:
“高山之巅有一条河,河水笑着望着山坡。昔日它从你脚下经过,今天它又从你头顶经过。”这首诗是华国锋主席写的。
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听着我的讲课,有时仰望黑板上方的毛主席和华主席的画像陷入沉思;有时露出如花般灿烂的笑脸。
上体育课时,没有器材,我只能带领学生跑步、跳绳、打毽子;以及玩扔手帕、捉迷藏等游戏。
音乐课上,学生在没有乐器伴奏和乐谱的情况下,自己唱,但老师和学生都充满欢乐和激情。《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红歌,老师教一遍,学生就能唱一遍,有的学生唱得比老师还好,甚至拍手打节拍。
在教学点上课,整天和七八岁的孩子们在一起,感觉就像回到了童年,我并不觉得工作单调、繁重,心里想的都是尽自己该尽的责任。
2. 在主校区
主校区多栋危房被拆除改造,教学点三年级学生返回主校区上课。
1977年秋天,我离开教学点,到校本部担任初一数学老师。
站在校园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学校成立时,师生们在房前屋后栽种的白杨树,如今高大挺拔,随处可见碗口或桶口宽大的树干,像忠诚的卫士一样日夜守护着学校这片圣地。教室门前的乒乓球桌,青砖底座支撑着蓝漆水泥面,比过去的土台美观多了。会议室窗外悬挂的二郎庙旧铁钟,也换成了小巧玲珑的新钟。操场中央的木质篮球架,也换成了全新的钢架。
现在的学校已和以前判若两人,小学三年级有15个班,初中二年级有4个班,学生有八九百人,教师有42人,是公社里为数不多的较大规模的学校之一。
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用的数学教材是“苏教版”,是江苏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章有理数;第二章方程式和等式。一般上午第一、二节课上课,下午批改作业、写教案,每天机械而又有趣的重复。
寒冷的冬天,早餐吃着两碗红薯粥、一个红薯馒头,顶着西北风马不停蹄地步行去学校,浑身暖洋洋的。在教室里连续站了两节课,浑身更是暖洋洋的。现在说辛苦,那时候可真没感觉。
在主校区,一切都给人清新、美丽的感觉。
更妙的是今年的十月,天空特别晴朗,河水特别清澈,谷粒特别芬芳,菊花特别芬芳,我与社会上许多老师、青年一样,怀着同样的美好愿望,复习、准备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
还记得当时作文题目是《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数学题有“等差数列”应用题、“指数与对数”等计算题,物理和化学题现在记不清了。
可惜,我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希望没有实现,不过我也松了一口气,被选中参加政审和体检,虽然没有成为天之骄子,但心里还是很满足的,那个年代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参加高考,憧憬美好的未来,这也是青春的珍贵回忆,人生的一笔财富!
学校会议室在前任校长的指导下更新了新内容:
正面山墙正中,毛主席、华主席巨幅画像两侧的标语,仍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又增加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等新的标语。
后墙上面正对着门的墙上挂着一些自制的镶框玻璃标识,上面不仅有原有的政治学习制度、教学工作制度,还有新增加的业务学习制度、作业和教案检查制度、签到和离开制度等。
最难忘的是秋季学期的期末考试,这次考试由全公社统一组织、统一监督、统一评分。
可能是我能力有限,也可能是忙于高考复习,没空教书,我教的两个班的考试成绩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全社排名一模一样,一个班排在最后,一个班排在倒数第四。
这样的成绩让我汗颜,虽然领导没有批评我,但我心里却感到深深的愧疚,羞愧面对提拔我的老校长。
青春的激情,就好比深秋的野菊花,正盛开着,却遭遇突如其来的重霜,而后枯萎,与此同时,也在默默地积蓄力量,迎接新一轮花期的到来。
3. 回到教学点
1978年秋天,我回到了教师岗位。
在教学点,我经历了一件令我难忘的事件,它影响并决定了我的教学生涯。
10月份,南阳县教育局开始对县内民办教师进行整顿,老河公社刘校长来我校指导整顿工作,整顿主要针对听课、考试两个方面。
我在教《国际歌》这节课时,我设计了这样的导语:“这节课,老师带领同学们唱一首歌,好吗?”
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好!”
“起来吧,你们这些饥饿、寒冷的奴隶;
起来吧,世上受苦受难的人们!
我的血液在沸腾。
为真理而战!
旧世界已成废墟……”
我唱,学生们唱,正在听课的领导也唱。
“我们要成为世界的主人。”我这样向我的学生解释“主人”这个词:人有饭吃,有学问要读,有工作要做,这就是“主人”的意义。一个勇敢的学生说:
“老师,我也是大师啊!”
“是啊,我们同学每个人都是师父!我们的父母也是师父!”
我听到刘校长低声对随行的教务长和总务长说:“这个小伙子很会讲课,而且讲得好!”
期中考试结束后,我和同事们一起参加了县教育局组织的文化考试,我的成绩在全校老师中名列前茅。
整改工作已经结束,我通过了课堂和文化两门科目的考试,很多比我教龄长、工作能力强的同事,因为课堂成绩不好、考试成绩不好,没有被选为计划中的民办教师,和这些同事相比,我是幸运的!
这个出乎意料的考核结果,让我曾经冰冷的内心重新燃起了激情之火,更加坚定了我终身当老师的信念。
4. 回到学校主校区
1980年秋天,老校长把我调回主校,让我教初中二年级的数学,这个学期,初中由两年制改为三年制。
从这个学期开始,我感觉学校的教学和管理比以前严格了很多,学校每周都有例行的工作检查,每个老师的教案、学生作业批改都要检查,检查完之后,好的在例会上表扬,差的校长要个别谈话。学校领导听老师们的讲课,有时候事先通知,有时候不通知。校长、教务长、其他老师都可以旁听。
这些管理给每一位老师都增加了压力,压力变成了动力,老师们自觉地留校上课、熬夜学习,提高教学质量。
说到住在校园里,一件我不想发生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照例吃完饭去上课,拿出钥匙开门,却发现锁不见了。推开门,用手电筒照了一眼,吓了一跳!床铺不见了。有的同事说,一定是村里一些形迹可疑的流氓干的,有的说,可能是班里一些坏人干的。众说纷纭,谁也说不通。老校长见此情形,叹息一声,咂着嘴说:“真冤枉啊!真冤枉啊!”事发后不久,大队给我送来了10米布券、10公斤棉卷;学校又给20元钱。那个冬天,我没有感受到寒冷的天气;却得到了大队和学校的关爱温暖。
1981年1月秋季学期结束,该校属下两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回学校看望教师。
老党支部书记张爷爷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承包责任制,调动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今年大队决定给每位教师发50元奖金!”
这时,会议室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年轻书记何叔接着老书记说的话:
从今年开始,该村将土地分配到户,进一步提高群众生产劳动积极性。
两位支部书记的励志讲话,让我和各位老师同事们重新燃起了转正的希望。
每天,从家到学校,从学校回到家,我走在人杰地灵、风景秀丽的家乡的土地上,走在浸透了先烈鲜血的家乡的土地上,走在吹拂着改革开放春风的家乡的土地上。
不知不觉,我已经当老师六年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删除。
(本平台所有文字均为原创,如有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吴延东,男,河南南阳人,退休小学教师,现居深圳。作家地带签约作家。